凤凰文艺版 《傅雷家书》序
毕飞宇
2008年的4月7号,是傅雷先生的百年诞,南京大学举办了“傅雷诞辰10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世界各地来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家,许钧教授关照我去会议上去说几句话。这个我可不敢。我不会外语,是个局外人,哪有资格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五人六。许钧对我说,你还是说几句吧,傅聪专门从伦敦赶来了。一听说可以见到傅聪,我即刻就答应了。关于傅聪,我的脑子里是有形象的,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,我的父亲曾经送给我一本书,那就是著名的《傅雷家书》。
《傅雷家书》当然是家书,可是,在我的眼里,它首先是一本小说,主人公有一共四个,傅雷,朱梅馥,傅聪,傅敏。我为什么要说《傅雷家书》是一本小说呢?——从头到尾,这本书到处都是鲜活的人物性格:苛刻的、风暴一般的父亲,隐忍的、积雪一样的母亲,羸弱的、积雪下面幼芽一般的两个孩子。楼适夷说“读家书,想傅雷”,然而,在我,重点却是傅聪。我的父亲出生于1934年,他告诉我,同样出生于1934年的傅聪“这个人厉害”。我当然理解父亲所说的“厉害”是什么意思,这个天才的钢琴家在他学生时代就做过惊天动地的“大事”了。我对傅聪印象深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那时候我正在阅读傅译本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,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里头有一个诗人——奥里维,他才华横溢,敏感,瘦弱,却可以冲冠一怒。我认准了傅聪就是奥利维,而奥里维就是傅聪。
就在南京大学的会议室里头,当许钧教授把我介绍给傅聪的时候,我很激动。当然,正如一位通俗作家所说的那样,毕飞宇这个人就是会装。没错,我就是会装。我控制住了自己,我很礼貌,我向我心仪已久的钢琴大师表达了我应该表达的尊敬。当然了,遗憾也是有的,傅聪一点都不像奥里维,傅聪比我想象中的奥里维壮实多了。
在那次会议上,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,我想我的发言跑题了。我没有谈翻译,却说起了《傅雷家书》,我从《傅雷家书》里读到了许多,但是,最感动我的,是爱情,是傅雷与朱梅馥不屈的爱。——感谢楼适夷先生,如果没有楼适夷的序言,我不可能知道这个。朱梅馥是在政治高压里头“伴随”着傅雷先生而去的,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“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”。这是骇人的,他们的死凄凉、沉痛,同时也刚毅、悲壮。虽然我不想说,可我还是要说,他们的死固然骇人,但是,它也美,是传奇。斯人已逝,日月同静,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
有一句话我在发言的时候没敢说,傅聪先生就在台下,话在嘴边我又咽下去了:同样是右派的儿子,我却很幸运——我的父亲活下来了,是我的母亲陪伴着我的父亲一起活下来的。
还有一点需要补充,就在当天晚上,就在傅聪的答谢音乐会上,傅聪发脾气了,说暴怒都不为过。有人在音乐厅里大声地说话,不停地说话,肆无忌惮。傅聪在演奏,却侧过了脑袋,他在怒视。最终,傅聪抬起了胳膊,他停止了演奏。他站了起来,他来到了台前。他的脸涨得通红。因为没有麦克,他大声喊道:
——请尊重音乐!
——你们再说话我就不弹了!
是的,这是傅聪。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男人就是傅聪。他儒雅,通身洋溢着大师才有的亲和。但是,傅聪也刚烈。这是傅家祖传的刚烈。傅家的人容不得亵渎。傅雷还活着,就在台上,他站立在傅聪的骨架子里头。
在我十七岁的那一年,也许还不止一年,我被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缠住了,仿佛鬼打墙。严格地说,是被那种庄严而又浩荡的语风绕住了。“江声浩荡,自屋后上升”,上帝啊,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,这太迷人了。迷人到了什么地步呢,迷人到了折磨人的地步。就在阅读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的时候,我特地预备了一个小本子,遇上动人的章节我就要把它们抄写下来。在我读完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的时候,小本子已经写满了。我是多么地怅然。怅然若失。完了,没了。挑灯看剑,四顾茫茫。有一年,青年批评家张莉女士来南京和我做对话,我对张莉说,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里头的许多句子我能背。张莉不信,她让我背给她听。后来张莉打断了我,她说,我信了。
对不起,我不是炫耀我的记忆力。我要说的是这个——有一天,许钧教授告诉我,罗曼·罗曼的原文其实并不是中国读者所读到的那个风格,这风格是傅雷独创的。许钧的话吓了我一跳。老实说,我一直以为翻译家和作家的语调是同步的,原来不是。许钧教授的话提升了我对翻译的认识,翻译不是翻译,翻译是写作,翻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,至少,对傅雷这样的大译家来说是这样。翻译所需要的是创造性。许钧教授的一句话我引用过多次了,今天我打算再引用一遍:“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家,那就是一场艳遇。”是的,在谈论罗曼·罗兰和傅雷的时候,许钧教授就是用了这个词——“艳遇”。我相信,只有许钧这样的翻译家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它精准、传神,惊天动地,荡气回肠。文学是迷人的,你从任何一扇窗户——即使是翻译——里都能看见它无边的风景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
四十岁之前,有无数次,每当我写小说开头的时候,我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——“江声浩荡”,然后,然后当然是一大段的景物描写。等我写完了,我会再把这一段毫无用处的文字给删除了。这四个字曾经是我起床之后的第一杯咖啡,它是我精神上的钥匙,也是我肉体上的咖啡。我能靠这杯咖啡活着么?不能。我能不喝这杯咖啡么?也不能。孟子说: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,我不敢吹牛,说我的身上也有浩然之气,我只是喜欢。但是,雨果的身上有浩然之气,巴尔扎克的身上有浩然之气,罗曼·罗兰的身上有浩然之气,傅雷的身上也有浩然之气。它们在彼此激荡。有诗为证——
傅雷先生洋洋500万字的译本。
足够了。
敦矣,煌矣。
噫吁嚱,危乎高哉。
我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,对我,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,傅雷是特殊的。我致敬傅雷。
有一种假设,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习惯,把自己放到读过的书里头,然后去假设。——再一次读完了《傅雷家书》,我的假设是,如果我有幸成为傅雷的儿子,我愿意么?
很抱歉,我一点也没有冒犯傅雷先生和傅聪先生的意思,我不愿意。
虽然毫无可比性,可事实上,作为同样的右派,我的父亲也是傅雷那款性格的人。这里头既有文化上的共性同构,也有性格上的私性同构。——苛求自己,苛求儿子,同时兼有道德上的洁癖。可以说,我对傅雷父子这么感兴趣,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,我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乡村版的、微型版的傅雷。面对自己的孩子,尤其是男孩,他有宗教一般再造的激情与布道的耐心。我的父亲之所以没到傅雷那样的程度,完全是因为他本人没有抵达傅雷那样的高度。对孩子,他的心没有那么大。此乃吾幸。
可是,话又要分两头说,如果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天才,狂暴的父亲往往会成为孩子的催化剂,从这个意义上说,傅聪延续了傅雷,傅雷成就了傅聪。我的父亲则很遗憾,他生下了了我这么一个二货。——以我父亲的设想,他希望我成为一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,西装革履,恬淡如水,不食人间烟火。可我哪里是学数学的料呢?结果呢,一场惨烈的家庭暴乱之后,我带上我的文学梦私奔了。一去无回。在这个过程里,我经历过一场很异样的痛苦,是家庭伦理意义上的痛苦。这也是我特别喜爱《傅雷家书》这本书的原因。抛开美学话题、音乐话题和道德话题,我愿意把《傅雷家书》当作家庭伦理的教科书。在梳理父子关系方面,这本书堪称典范。往正面说,我们可以获得方法,往反面说,我们可以获取教益。
我还要说,虽然我不是基督徒,可我还是相信上帝的仁慈和上帝的掌控力。上帝会安排的。上帝给你一个霸道的父亲,一定会给你一个天使一样的母亲。如斯,地方、天圆,五彩云霞空中飘,天上飞来金丝鸟,我们有福了,人生吉祥了。
我的建议是,所有的父亲都要读《傅雷家书》,所有的母亲也要读《傅雷家书》,所有的儿子更要读《傅雷家书》,只有做女儿的可以不读——在你成为母亲之前。
说到望子成龙,我还有话说。傅雷是望子成龙的,我的父亲也是望子成龙的。他们都是右派。我想指出的是,当年的右派大多是文人,说得科学一点,大多是人文知识分子,他们的基础性工具是语言。他们望子成龙,可他们为什么就不希望子承父业呢?为什么就不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语言呢?
我的父亲给了我这样的答案:希望孩子“安全”。
数学是“安全”的,物理是“安全”的,音乐也是“安全”的。最不安全的东西是什么?是语言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语言是精神的落地窗户,它一览无余。所以,让孩子学数学,让孩子学音乐,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父性的苛刻,骨子里是爱,是聪明的爱,是理性的爱,是恒久的爱,也是无奈的和卑怯的爱。
所以我要讴歌父亲,尤其是以傅雷为代表的、我们上一代的知识分子父亲。他们承担了语言的艰难与险恶。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妥协。他们看到了代价,却没有屈服于代价。具体一点说,他们付出了代价。这是惊天地和泣鬼神的。
所以我要讴歌母亲,但是,我绝对不能赞同朱梅馥女士的行为。你是傅聪的妈妈,你是傅敏的妈妈。即使满身污垢,你也要活下去。妈妈们活着,只有一个理由,为了孩子,而不是为了丈夫们的真理和正义。这是天理,无需证明。父可杀,不可辱;母可辱,不可杀。
最后,我要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黄小初先生,感谢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我自知力所不及,但我倍感光荣。
2017年2月7日于龙江寓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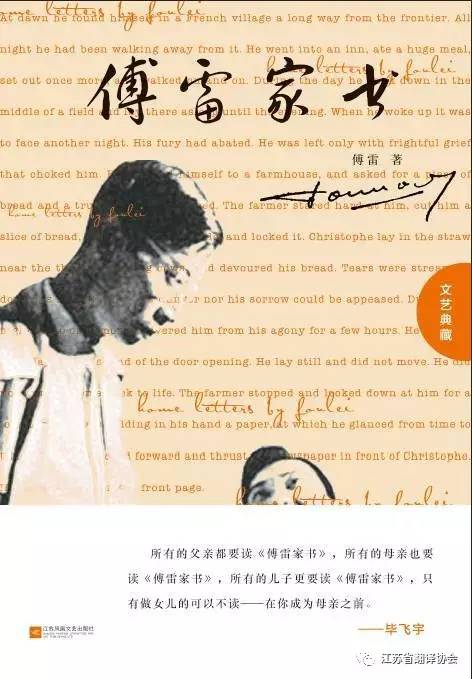
《傅雷家书》